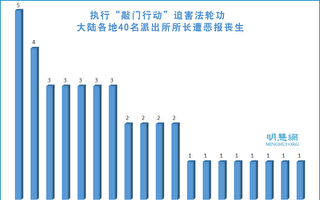【大纪元2018年12月17日讯】谢燕益,中国知名维权律师,因仗义执言,屡遭中共打压,上月又被当局注销律师执业证。以下是大纪元特约记者对他的访谈纪要。
记者:您刚刚被注销了律师执照,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谢燕益:“709”事件我被关押了553天,是被取保放出的,然后我发表文章,接受采访,继续为自己、为“709”弟兄们及一些冤狱奔走呼告,他们会觉得我“不听话”吧。尤其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案子,因为此案有国际影响,超过十个律师曾被官方通过各种方式威胁,最后都被解除了代理。
今年5月律协就调查我,害怕我作为孙茜的辩护人出庭,庭审那天,我去现场参加旁听,他们竟然不许我进去。
他们注销我的执照,是因为害怕。为什么会害怕我?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制造冤狱的,作为孙茜代理律师,我见证了这个过程。
有人害怕这个国家走向正常,“709”后,对律师的打压仍在继续,但凡和官方“死磕的”、坚持说真话的律师,就会受到警告整肃,甚至被吊销或注销律师执照。
记者:您可以讲讲孙茜目前的情况吗?
谢燕益:现在,他们居然采取威逼、欺骗的方式,迫使孙茜放弃律师、放弃自己的财产、放弃自己的信仰,甚至放弃自己的加拿大国籍!你可以想像吗?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!
据我知道,昨天又有家属聘请律师见孙茜,她表示不见。最后在律师坚持下,孙茜带着黑头套被押过来,对律师只说了一句:“我不需要律师,我已经有了政府给我指定的律师。”扭头就走。
为什么?匪夷所思啊!她被抓捕后,遭受过酷刑,坐过老虎凳、灌过辣椒水,可以想见,为达到目的,他们还用了其它软硬兼施的手段,非常卑鄙的。
现在需要在国际上为孙茜呼吁,中国司法整个被血债帮绑架,不可能有一个司法公正的结果了。在外交层面上,加拿大政府应该对此事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,应该保障她的人权。
记者:你被取保后三天,就向外界曝光了里面的酷刑,您不害怕再被抓进去吗?
谢燕益:释放我之前,他们无数次威胁我:“不准见记者,不准曝光,不准写文章,否则还会把你抓回来,你的家庭也不会安全,都没有好结果!”
我个人曾遭受了饿饭、不让睡觉、扇耳光、殴打、虐待等迫害。2015年10月1号到10月10号,我还听到了楼上有人遭受酷刑,似乎是电击,有重重摔到地上的声音,呻吟声、哀求声,我都听得清清楚楚,现在看来,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师当时在遭受酷刑。
在里面时我对自己有过一个诺言:如果出去,一定第一时间把里面的酷刑披露出来。所以回来头三天,我一直睡不着:曝光还是不曝光?怎么曝光?
妻子虽也是性情中人,喜欢仗义执言,但不希望我再参与这些事,她已经承受太多。我很矛盾,一家人的团聚来之不易,我们要抚养三个孩子。
在里边,他们给我看儿子的录像,还有刚出生女儿的照片,多次以此劝降:不要太自私,想一想你的孩子。我觉得两个儿子经历一些苦难,对成长未必是坏事,但对我的女儿,确实不公平。由于我的选择造成的伤害,最后竟是由孩子来承受!
但不曝光我对自己没法交代。我非常害怕,非常焦躁,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人面对了一个世界。说心里话,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,灭顶一样的压力,至少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,真的非常害怕。
选择是很艰难,但任何代价都不能用良心来交换吧,这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理由。其实很多人,包括那么多大法弟子、一些政治犯,在这种煎熬中,不也都选择了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吗?
所以出来第三天,抱着要再进去的想法,我把酷刑披露出来了。
记者:您可以谈谈您的“选择”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吗?
谢燕益:我在里面时,两个儿子的遭遇就不说了,举个我出来后的例子吧。我因参与法轮功的案子被报复,被调查听证,和警察发生了冲突。被摁在警车里的时候,我听到了女儿的哭声,那时她才2岁,我在车里很难受,这是我接受不了的。我女儿看着他爸爸被警察带走,后来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妈妈。而爸爸和妈妈是最能保护她的。
我接受不了不是因为我受到凌辱,而是为我女儿难过,她在妈妈肚子里时,她妈妈就被抓进派出所,不给饭吃,不让休息。从她出生的第一天,她妈妈就被逼迁,她跟着妈妈流离失所,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!
我无法和女儿解释,这种苦痛惊吓只能由遗忘来医治。我女儿特别特别懂事,自来熟,见人就主动示好,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。正面的理解她是适应环境,负面理解,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。
这就是天天发生在中国的现实,作为一个律师,我还被媒体报导关注,但有多少上访户、法轮功学员、政治犯,他们被绑架被残害,死在监狱里面,并没有人关注!
记者:“709”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关吧?
谢燕益:其实我性格是比较被动的,做律师天天接触冤狱,都有些麻木了。
而恰恰那时,跟徐纯合一样,我也是孩子的父亲了。我看到徐纯合暴尸在火车站,旁边围着他的三个小孩和年迈的母亲,官方说他抢枪袭警,他是被当作恐怖分子在孩子老人面前被击毙的!他能拖家带口去袭警抢枪?
同为人父为人子的角色让我无法接受,所以我仗义执言,先是从技术层面分析了现场,发了检举警察涉嫌故意杀人的法律意见,没想到网上迅速发酵。网友又给了我他母亲的电话,我更不能推卸责任了,第二天我就义无反顾去了庆安,明察暗访,并把真实消息发到了网上。
接着全国各地的很多网民和律师都赶往庆安,去声援,去举牌抗争,他们不计个人安危,不约而同到庆安,其实是一种愤怒的爆发。
从庆安回北京后,央视就定调了,说民警的枪杀是合法正当的。于是我和谢阳等几个律师又起诉央视,这成了“709”的导火索。
其实我就是比较较真,尊重事实、尊重法律,我的人生福祸都因为这个吧。
记者:您不觉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样?很多人认为能过好自己的日子,为家庭负责就行了,岁月静好。
谢燕益:现在的中国,食品、土壤、水,甚至你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,避无可避啊,就是挖个耗子洞钻进去,你都躲不了祸,你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吗?哪有岁月静好?
1949年以后,集权造成的人道灾难屡见不鲜,每天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,只是命运没有把你摆放在那儿。如果你不去面对,那这不幸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,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伸头一刀、缩头一刀,有了老婆孩子以后,我作为父亲,作为丈夫,尤其作为一个律师,没有别的选择,我们不面对这个险境、不去讲真话,不去追究违法犯罪,社会就会继续烂下去,那大家迟早都会遭殃,对于我的子孙后代,我认为也是在负责啊。
如果有人认为岁月静好,他肯定要有一个扭曲的方式来应对,防范被伤害,他才能存活下去。他是正常人吗?坚持自己的原则,不愿意同流合污,不愿意被扭曲,反而被社会边缘化,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!到底是我不正常,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?

对于强者来说 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
记者:可是您觉得您能改变现实吗?
谢燕益:我相信心念造物,一诚动天下,这个国家是我们一闪一念造成的共业,改变不了现状,可能因为我们诚意不足,意念还不够坚定,正念还不足够吧。
我发表文章,写法律文书及辩护词,都尽量站在善的立场,周永康也好、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,枪杀徐纯合的警察,包括背后的黑手,我都希望他们能醒悟,得到救赎。你昨天作恶,今天停止,马上积功累德都未为迟晚。我相信善的力量无往而不胜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。
一般我不会轻易投入一个案子,但既然投入,做律师,受人之托忠人之事,我会力所能及不违背自己的良心,做我该做的,做正确的事,无愧无悔。至于说结果,一切交给上天,一切都有定数,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,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。
记者:您在文章中写过“40岁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龄”?
谢燕益:进去之前,我就写了我的座右铭: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,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。
我认为,如果太早经历了不堪承受的苦难,人可能会被扭曲、打垮。而40岁的我,历经了人生的各种无常,在知识上已有积累,对人性、社会、历史都有了比较深的感悟,所以被抓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:磨难来得正好,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,是灵性觉醒、生命升华的一个条件。对于强者来说,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,从我个人的命运来讲,我觉得磨难是上天对我的恩典。
对一个族群也是这样的,我们这个民族,历经了这么多苦难,经历了文革浩劫,但很多人还没觉醒,还没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。我们能不能对得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?
记者:现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与律师同行都不一样?您会有孤独感吗?不能做律师了,您不担忧以后的生活吗?
谢燕益:经历了“709”,现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师还是其他人权律师群体,大家都有不同的选择。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使命,做自己的事情,也就是这样的。
我一向都有点孤独,早在2003年我起诉江泽民,那时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,后来包括推动和平民主、参与维权案件,我都觉得自己是孤独的。区别就是,“709”之前我还耐不住孤独,不甘于寂寞,现在我很享受孤独了,这种孤独不是坏事。
之前我可能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认可、建功立业等等,之后我对这些能淡然一点了。穷则独善其身,现在我更关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,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,而不是外在的东西。出来之后,我每天都坚持打坐2个小时,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
我会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,为社会、为别人。职业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,决定人未来的还是自身的不断觉悟,能不断地去面对,去勇于承担责任,而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对责任的担当。
我有三个小孩子,我们两口子的压力都比较大,但我觉得一切都会有安排的,你不会没有事情做,你也不会没有饭吃,道心之中有衣食,衣食之中无道心。
我们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
记者:听说您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,她应该很懂法律了,生前她难道不认同您吗?
谢燕益:首先,我母亲从小就没有安全感。当年我姥爷为了找出路,参加了中共党搞土改,进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,找了小20岁的“革命的伴侣”结合了。那时我母亲还非常小,心里肯定有阴影的。
文革时,她也特别恐惧,不知道是跟着人贴大字报还是不跟着人贴,后来她参加了武斗,被打得眼冒金星,恐惧。后来她成为中国最早的律师,又因为不够圆滑被当地司法局排挤。
我起诉江泽民的时候,母亲和我断绝关系,不让我在家里住,她不是不懂法律,她恐惧。我被抓后,她恐惧,一个月后就很快离世了。一直到去世前一天,她还订阅中共的报刊,家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书。她大量高价收购纪念毛泽东的书,还有像章,多贵她都要,喜欢,实际上也是恐惧。
我母亲根正苗红,作为被中共被彻底洗脑的老党员,她崇拜毛泽东,把毛泽东当作父亲,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,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场上,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她认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给的,她意识不到她是共产运动的受害者。她没有能力爱别人,不接受任何人的爱和善意,对人性深度怀疑,甚至连天性都快丧失了。为了所谓的革命,不管家、不管孩子,甚至亲人的生啊、死啊,都无所谓,她内心深处都被扭曲了。
按照传统,陈世美抛弃妻子是令人不齿的啊,传统美德讲糟糠之妻不下堂,我姥姥给姥爷生了这么多孩子,姥爷竟能抛弃她,禽兽不如嘛。当时很多党员进城后都找借口这么干的。那些所谓的“地富反坏右”是被中共直接伤害的,跟着中共的,像我姥爷这种人,也是被它毒害的,被它的谎言蒙蔽,相信唯物主义、斗争哲学,为了革命无恶不作,以“革命”这种高大上的名义,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,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。
我的家庭里,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,我姥姥是受害者,我母亲是受害的,我姥爷也是!
每个中国家庭,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乌托邦红祸的毒害。你去发现吧,母亲父亲,爷爷奶奶,你的亲人里边,如果人格上有问题,偏执,或缺乏爱、缺乏善、缺乏包容,都有仇恨这种东西,一定是受到了共产极权的毒害。
我懂事以后才反思这些,现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,我和我太太吵架,极端的时候也打孩子,这里面都有仇恨,有性格里那种偏激的东西,都是红祸运动的毒害。
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华一样的人,他们又何尝不是专制极权的最大受害者?尽管他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,但从我个人来说,我愿意原谅他,他也有妻儿老小。在中国,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
这个体制扭曲了所有的关系,父母和孩子,丈夫和妻子,朋友的关系,现在都被异化扭曲了。但人性中的良善,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给人洗脑就能彻底抹杀的,我太太就有那种先天的贤惠。
记者:那您怎样让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脑教育呢?
谢燕益:集权体制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,红二代官二代生下来就比你有钱、有权,有更多教育、就业的机会,而我们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间。
我们不得不珍惜一点一滴夹缝里的机会。一方面,孩子能上学,我们就感觉庆幸了,它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不让我们孩子上学。另一方面呢,我很无奈,没有办法,极端功利的应试化教育、扼杀人性,红色的洗脑,假大空,什么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,还有一些伪道德,什么伟大复兴、中国梦什么的,都跟自然科学、常识、数学、语文、英语捆绑在一起。你能让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?不要听老师的话?可能吗?不让孩子系红领巾?不系红领巾孩子连学校的门都不让进!
这些系统的洗脑,无孔不入渗透在生活、学习、教育、就业的方方面面。这个历史被篡改了多少?法律层面上有多少意识形态的东西?宪法里掺杂多少政治私货,有多少一党一派的专制余毒?但它以伪善的面貌出现,它站在道义高地上,不要说孩子,就说大人,有多少能识别?
现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让我的两个儿子打坐、修炼,相信神明的存在,有敬畏之心。

记者:您似乎特别喜欢“和平民主,天下为公”这八个字?
谢燕益:“和平民主,天下为公”这幅字,是我专门请一个叫陶禾子的朋友写的,他是大法弟子,妹妹因法轮功信仰被绑架迫害,判了三年。我曾经给他妹妹辩护。这几个字就是我对中国社会的展望了,追求国家的和平转型,追求一个人权至上、文明法治的国家,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。
附:谢燕益近年经历
谢燕益,43岁,祖籍广东电白,
2003年,谢燕益起诉江泽民,起诉他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。
2015年5月,到哈尔滨庆安调查“庆安枪杀案”,后与众多律师向中共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举报警察涉嫌故意杀人,这成为“709”事件的导火索。
2015年7月被抓捕,罪名为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,553天后出狱。
2017年,代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法轮功信仰案。
2018年11月,被注销律师执业证。@*
录音整理:大纪元特约记者孙居正,责任编辑:苏明真